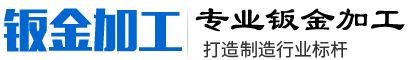HASH GAME - Online Skill Game GET 300

王家卫用他高饱和度的摄影和抒情影调,创造了一个未必再现历史真实,却高度浪漫化、传奇化的1990年代上海。作为最富国际声誉和个人风格的华语导演之一,王家卫不同于侯孝贤、杨德昌、许鞍华、贾樟柯等人追求写实性,他的影像语法极其华丽、迷离,从善于使用大牌明星和渲染城市魅力的角度来看,他又像一个艺术电影圈的“广告”大师。他把一种“怀旧病”嫁接入小资的敏感和布尔乔亚的迷惘。出生于上海的他,成为香港的城市名片,当他试图再现昨日的上海时,有评论者却说,他拍的上海也像香港。
自19世纪末以来,上海逐渐成为与北京双峰并峙的中国两大文化中心之一。《万国公报》《申报》登场,吴趼人(“我佛山人”)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进入民国,海派与京派各领风骚,电影则成了这个城市新的魔法。即使多年之后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来到了海峡对岸,上海仍是这组群像挥之不去的巨大背景。1924年,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小说中把上海称为“魔都”,这一命名意外地在互联网时代获得新生。一种跨越百年的关于上海的城市情结,借着《繁花》再度风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差不多二十年前,我们担心上海的文化、影视、文学陷入低潮,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曾经一度陕西出的作品都要比上海好。这几年上海无论文学还是电影,开始了复苏,出现了沪语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爱情神话》,小说和剧版的《繁花》。上海的艺术、年轻人的文化,也是领先全国的。”在许纪霖看来,上海是全国城市里最适合city walk的,特别是浦西的老城,晚清民国风貌的建筑,几乎每一座楼房都有灵魂和故事,而文学、影视作品流行之后与旅游的互动,上海恰好也走在了前面。
从《神女》《马路天使》《哀乐中年》到《苏州河》,上海始终是中国百年影史上浓墨重彩的城市舞台。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知名的港台导演热衷于拍摄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的影片,如关锦鹏的《阮玲玉》、许鞍华的《半生缘》、李安的《色,戒》,后两部都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改编自琼瑶小说《情深深雨濛濛》的电视剧近年来再度被热议,1930年代的上海,成为一座可以反复抵达的想象中的都会。即便是豆瓣评分仅有5分左右的“小时代”系列,也以架空的形式,执拗地创造了一个作者理想中泛着彩色泡泡的上海。
在有声电影刚刚取代默片的时代,许多电影界人士忧虑电影会成为文学的附庸,电影将失去艺术的自足性,成为经典文学故事的传声筒。但《百年孤独》的影视化恰恰说明,今天真正失去自足性的,可能是文学本身。一部文学作品被影视化,一方面意味着原作的死亡,正如今天我们想到《红楼梦》,很难不先想到87版《红楼梦》里鲜活的形象,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杀死”文本中自由的、不被任何形象所束缚的林黛玉;另一方面,影视又“复活”了文学,中世纪的欧洲人要借助教堂的壁画,而不是《圣经》本身来了解那些故事,今天的人们虽已普遍具备读写能力,却再度被视觉化、景观化的影音制品褫夺了注意力,这一过程将不可逆转。
然而,许多游客却在小红书上发帖对比“我以为的阿勒泰”和“实际上的阿勒泰”,“网络上”和“实际上”的禾木村、巴太树、剧中取景的小卖部,通过巨大的落差来表达失望。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官方微信号“喀纳斯零距离”发布的《关于喀纳斯景区旺季最大承载量的公告》显示,为保障旅游者人身安全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测算确定喀纳斯景区旺季(每年5月1日至10月15日)日最大承载量为3.5万人,其中,喀纳斯日最大承载量1.9万人,禾木日最大承载量1.25万人,白哈巴日最大承载量0.35万人。有限的游客容量、难堪重负的基础设施,本身便与景区的“网红”化存在矛盾。
2024年9月上映的电影《出走的决心》引起热议,导演尹丽川虽是诗人出身,但这部电影并无文学剧本,而是取材于“50岁阿姨自驾游”的真实故事,阿姨因长期受到夫权和家庭的压抑而患有抑郁症,她为人所知,本来就源于社交媒体上配合照片和视频的自述。从动人的真实事件,到社交媒体,到电影,再回到社交媒体的二次传播,形成了故事的媒介化闭环。自驾游阿姨寻找自我,她行经的云南等地,也与影片中无穷无尽的家务劳动和辱骂的室内戏形成了强烈对照,旅行与出走成为掌控命运的隐喻。
李娟、金宇澄、邵艺辉的作品之所以动人,或许可以通过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来理解。李娟既出生在新疆、长期生活在阿勒泰,对于本地的哈萨克人,又具有外部视角,她对自然和民情的书写,具有一种人与土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天然去雕饰的美感。金宇澄是上海本地的“老克勒”,家长里短,都能用口语娓娓道来,所以入木三分。邵艺辉是这座城市的新移民,但她显然深深认同上海的“腔调”和这座城市提供的时髦、多元的种种可能。
段义孚在《恋地情结》的结尾写道:“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脚步从没有停止过。理想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各种不同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从根本上讲它可能会是两种相反的图景:一种是纯净的花园,另一种是宇宙。大地上的产育给我们提供生活的保障,而星空的和谐更增添了几分宏伟。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从面包树下的阴凉到天空之下的疗伤圈,从家庭到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在海边度假到欣赏繁复的艺术品,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如果说《繁花》和《好东西》想要描绘花园,《我的阿勒泰》则想描绘宇宙。创作者因为“恋地”,创造出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圣地”,被远方的人们向往、寻访,形成一个不断互动的辩证过程。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和微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滕威则对这些现象持审慎的态度:“数字媒体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甚至可以说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今日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全都由数字媒体先行建构过。我们读书、观影、吃饭、闲逛、旅行等等都要先打开一个或一些App去搜索,寻找攻略、经验,接受这些App算法的定制化推送,然后按照它们预设的符合我们‘经济’身份的档位去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去消费。”
“于是大家都去买同样的书,看同样的电影,挤去同样的餐厅,按照同样的路线去旅行,导致生活高度同质化。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打卡,消费一次无数人消费过的爆款,所以才有所谓‘特种兵式’的到此一游。旅行本是一种慢生活的方式,现在却成为快消品。尤其是消费降级的形势下,各种walk风靡其实就是低成本快消式旅行的流行。”滕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就是为什么各地文旅拼命在数字媒体上营销,打造网红城市,但城市经济的实际收益却未必能如人意。”